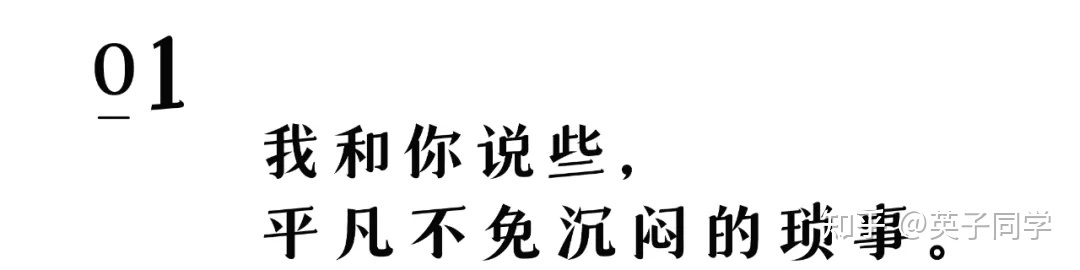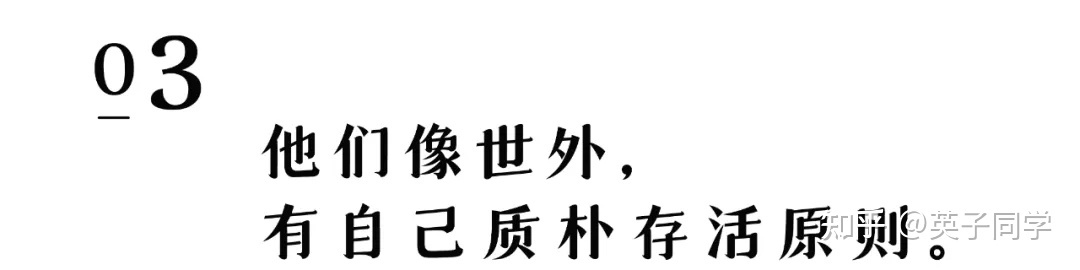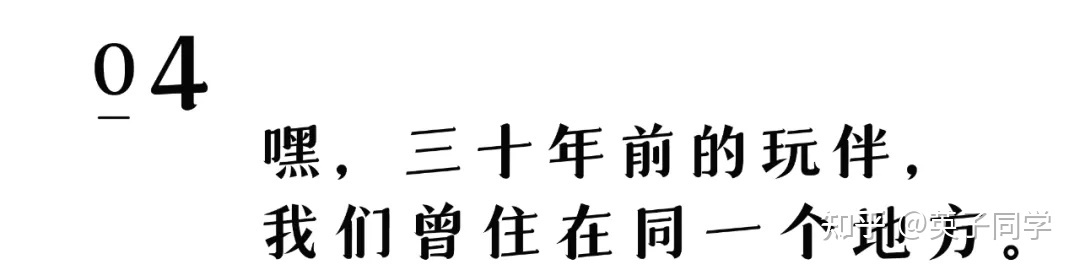|
库村,是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,保存完整中最大的一个古村。这个年纪最大的千年古村,和泰顺的其他古村落徐岙底、塔头底一样,瓦顶、鹅卵石的墙面、木结构。 早上的炊烟,从屋檐角落直冒出来,穿着一件解放工服外套带着帽子的大叔,骑着摩托车从这个村庄里出去了。 妇女从后门口倒了一脸盆水在沟里,再把门关上。修复宅院的工人,半掩着门,没有看到人,只听到敲打的声音。 进村口的水泥和流淌到路面的水,好像是村里哪户人家准备在前面做新房子了。
泰顺的百年古村走完了,库村和其他古村不一样的是:更古老、更大、村中现有居住的居民更多。 我看到有三户,院门前打扫得干净,贴上了大红对联,门口放着把竹椅,院子里种着鲜花、大葱、枣子或者其他的我叫不出来的小树。 我看到到了黄昏时,古村里聚集全了本地的村民,在鹅卵石的广场上,说着笑话,妇女们笑咧了嘴,笑出了龅牙……
三十年前,我也出生在这样的古村里,我们村里是典型的南方黛瓦青墙,卖豆腐脑、卖鱼的、卖蛋的每天早上和下午的间隙都听到他们的唤卖;在贫穷而破旧的村庄,我们总一起看着太阳藏在遥远的山上,日上三竿,各自的门前都洒满阳光。 那时我们还没有经历艰辛,更没有历经沧桑,只是却再也不会向以前那样,一人一根冰棍儿,嬉笑着聊着过往。
真是没有法子,我要和你说的这个地方,这个村庄,就是这样的,平淡沉闷,沉默的村庄。 村庄里充满了像我父辈、祖辈这样的人,面朝黄土,背朝天。 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活动,也不过是一日三餐和晚上的广场舞了。再不过是娶妻嫁女,丧仪这样的人生大事了。
不过像库村这样的村庄,特别的大事已经不会再在这个村子里发生了。嫁女儿般的喜事都会在村外的新房子里。 丧仪这样的事,还有可能发生在村庄里。因为村里的老人还在这里居住着,他们儿女有新的房子,但是他们还是喜欢住在像库村这样的老房子里。
这样的老房子门口,有自己侍弄了多年的红花,还有逝去老伴生前种下的枣树或者柚子树,蔬菜的篱笆都是他多年前做的呢,现在也只是修缮修缮。 这样的村庄,都是这样的人。依赖着土地,老得不愿意搬到新房子里去的老人。 也有特别的,赚的钱都供儿女读书,或者实在赚不到,实在没有钱建洋房,还居住在祖辈留下的这栋老房子里。
鹅卵石的道路从这户人家通往那户,通往了村庄里的库村书院,书院里有库村的历史,备好了茶具,是外来人经过介绍,来村庄坐一坐,和本地人攀谈的一个场所。 是文人墨客来这里,留下了自己的油画的展示,听说,也是一个老师的工作室。 我们从库村书院,找到了村庄和未来以及现在的某种微弱的联系。因为村庄还没有被开发作为商业运作,书院也是很佛系的,一般都没有开门,等通过熟人的介绍或者是电话。
鹅卵石的道路也通过村子后面的竹林,这些石头都是从河边搬过来吧,这样大,不像石头那样尖锐,比普通鹅卵石大几十倍。
层层堆砌来一个房屋,一个拱门,一座座的房子,泰顺多山,这在以前,村庄的称呼就和武侠里的山寨一样吧。
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大革命,没有一点矛头是指向这样的乡间,它们和哪一种革命都不沾边,因此, 哪一种革命也改变不了它们。 任何激烈的对峙都与它无关。外头世界的天翻地覆,带给这乡间的气象,便是像门口的河流走过一般。
这样的乡间,是很有情味也很现实的乡间。 他们永远给人出路,好叫人像这样的平凡地活着,一代接一代。
但是如果真的放任不管,这样的乡间你也是看不到的。你会看到的是出生地每一寸皮肤都被翻涌私自造烟的村子,老地基上建了4层不见人的高楼。 再也不会听到鸡叫、一到夜晚,都看不到村里房屋的光亮,一片漆黑。我只能在别人的故乡里寻找那记忆里故乡的形式。
我是多想哪天回去还能,我能有位奶奶,身体还精瘦矫健,在门口清理树上的杂枝,吃她做的霉豆腐,酿的米酒,尝下她养的家鸡蛋。或者妈妈也回到乡下,我也能吃到家里农家肥的新鲜蔬菜。 可是妈妈不会回去了,因为村里没有其他的妇人呆在家里,周围其他人的房子都建得高高的,没有人再会来别家串门,都在自己玩着WIFI,看着抖音,聊天的时候,也仅限于过年时分歇下来,坐在门口一起吃饭。 回不去了。
我在库村看到阿婆清理门口桥边的树枝,她快90了,耳不聋眼不花,院门口种着她的花。 门口摆着的化妆镜还是结婚时候带过来的吧,老式化妆镜的架子上再放着搪瓷洗脸盆。 应该是她的儿媳妇,把被子拿出来晾晒,对我们笑笑。
库村还有一户人家的,这户人家之前我来的时候在,他们家正在做午饭,南瓜和辣椒炒肉的香味飘了过来。 一位阿姨端着碗在门口吃着午饭。
平常日子,下午,村里的人呢要出去跑跑,房子就空在那儿。但是看上去一点都不虚乏,不散漫,不寂寞,不无主。仍旧是小,而充实。 若是时间稍久,一切,门堂,椅子,黄雀,老鼠,蝈蝈,伸进来是的一片阳光,阳光中浮尘飞舞。 所有的都在等待,等屋主人回来私自造烟的村子,等待把缺了一点甚么似的变为完满。乡村的人都去找出路,找到出路的人都还是想念平常那个日子的下午。
它们像是世外,有着自己质朴简单的存活的原则,自生自灭。 到了黄昏时,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。热闹在广场,乡民坐在凉亭里,说着笑话。早上出去的男人,回到家里的后门,此刻正在抽烟。 库村和其他古村落最大的区别,就在这个时刻。在这个由本地居民,组成的本地人才能听懂他们之间的笑话的时刻。
水草气味,淤泥气味,烧饭的豆秸烟微带忧郁的焦香,窗下几束新竹,给人一种雨意,人“远”了起来。 暮色悄然飘起时,该关门的地方就关了门,走出来的人们守时地匆匆往家赶,街上一下子见出了松弛慵懒和停滞。 各色灯光还不会那么匆忙地亮起,便由着那暮色肆意蔓来,悄悄然遮掩了白天过分的喧腾夸耀,村外的街道变得温柔安静起来,那点古朴之气就悠悠地弥散出来了。
已经全黑了,星星在天上。水草气更浓郁,竹声箫箫。水流,静静的流,流过桥桩,旋出一个一个小涡,转一转,顺流而下。我该回去了。
库村离我们住的农家乐只有一步之遥,整个新房子都把老房子包围。这种现象相比较我们把旧房子全部拆掉,好太多。 在库村里,就会想到小时候的事情。说真的,小时候的事情越是清切就越是辽远,令人愈是常想回去,但也许真的回去了,那些事又一古脑儿忘了。
我和我以前的发小们,从村庄里出来。我们同在一个城市,现在连简单的寒暄也变得寥寥无几。 而我们也很少回去,我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,还住在老房子的人。而我们的老房子,夹在一排排新房子的高楼之间,被遮挡了阳光,显得卑微而萎靡。 房屋与房屋前后的距离也越来越近,因为都想要更宽的房间的面基。可那更宽的面基里,也住得最多3个人罢了。
于是,我们留在了城市,我们有乡下的旧房子,没有乡下的新房子。即使我们有乡下的新房子,村庄也不在了。
挥别了青春,数不尽的车站,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腐烂。愿中国的乡村,村庄都好好的,人也好好的,希望库村更好好的。
我最喜欢黄昏时的乡民。 他们在黄昏时分也变了样,显得沉静了。他们似乎都是一个无知觉的整体的一部分,他们服从者一些只在他们脑子里隐约反映的冲动。
他们的眼光都是向着内心的,平平静静的;他们的眼睛也都在这黄昏时分发亮,在蒙着尘沙的脸上囧囧有光。 愿,每个人的明天,都像当年庄稼地头的阳光一样,灿烂! (责任编辑:admin) |